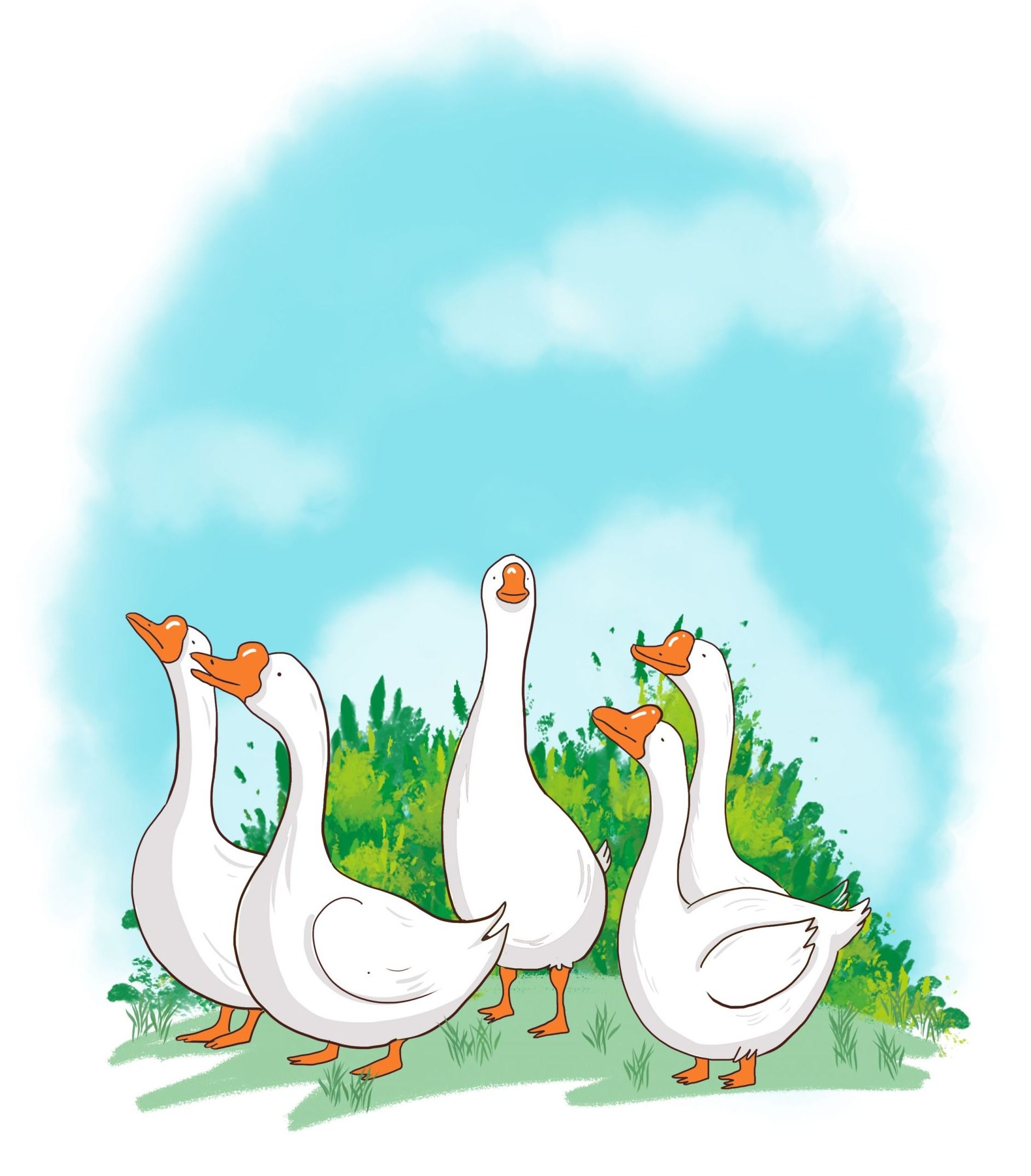 繪圖/鄭瑩
繪圖/鄭瑩
“鵝鵝鵝,曲項(xiàng)向天歌。白毛浮綠水,紅掌撥清波。”學(xué)齡前,雖然我還沒認(rèn)識《詠鵝》這首古詩,但已當(dāng)了兩三年“鵝司令”,對鵝的品性可以說是“了如指掌”。
我們村背靠“大山嶺”,東、南、西面皆為稻田環(huán)繞。每年二三月間,時(shí)有霏霏小雨,那些之前被翻犁起來“曬田”的泥塊長滿了馬蹄菜、一點(diǎn)紅、田基黃、鹽菜、田艾等,冬閑田變成了“百草園”,各種野草野菜鮮嫩欲滴。我將一群鵝兒趕到田里,它們自由自在地享受綠色大餐。鵝兒除了不吃田艾和“鵝不食草”外,其它草類通吃。鵝兒在快樂地吃草,我則在悠閑地摘田艾(做田艾籺用)。鵝兒吃草吃得香,邊吃邊“鵝鵝鵝”地叫著。待鵝兒們吃飽了,我的竹籃子里也盛滿了又嫩又香的田艾,真是皆大歡喜!
除了牧鵝,我還放鴨,當(dāng)“鴨司令”。鴨子生性喜水,早稻田里水源充足,成了鴨子“喜出望外”的游樂園。一到稻田邊,20多只鴨子就像士兵發(fā)起沖鋒一樣,一邊“呷呷呷”叫著,一邊飛快鉆入稻田,耳邊頓時(shí)響起一陣“噠噠噠”聲,好像打起了機(jī)關(guān)槍。稻田里有小魚小蝦、田蟹田螺、泥鰍塘鲺等,也有一些小蟲子,這些都是鴨子的天然美食。所以鴨子一鉆進(jìn)稻田,沒吃飽玩足,耗上兩三個(gè)鐘,它們是不肯鉆出來的。任憑你“哩哩哩”不停地吹響“集結(jié)號”,它們就是無動(dòng)于衷,忘乎所以。放鴨,最爽快的是“放”,最費(fèi)勁的是“收”——將它們一只不漏地召集回家。
與鵝相比,鴨的體形雖小,但由于它們活潑好動(dòng),故食量較大,除了外出放養(yǎng)時(shí)由它們自行覓食外,在家圈養(yǎng)時(shí)也要給它們“加餐”,一般是喂些番薯、菜葉、米糠之類。而養(yǎng)鵝則省事多了,平時(shí)不用怎么管它們,放牧?xí)r讓它們吃飽野草即可。
牧鵝,考驗(yàn)著人的耐性。鵝吃草吃飽后,要坐著小憩。即使你趕著它們往家里走,它們在途中也是走走停停,甚至一屁股席地而坐。只要有一只鵝帶頭坐在地上歇息,其它的鵝就紛紛效仿。有道是“急驚風(fēng)遇上慢郎中”,面對鵝的慢節(jié)奏,我這個(gè)“鵝司令”也無計(jì)可施,只能不停地?fù)]舞竹棍,催促它們快點(diǎn)跑。
如果把鴨比作先鋒官,性子急,喜歡打頭陣,沖鋒在前,那么鵝就是大將軍,不急不躁,喜歡在后面壓陣。鵝體型肥碩,它們走起路來搖頭晃腦的,那不緊不慢的神態(tài),真有點(diǎn)“不管風(fēng)吹浪打,勝似閑庭信步”的模樣。牧鵝放鴨,初衷是為了替媽媽分擔(dān)家務(wù),同時(shí)也放牧自己幼小的心靈。沒想到,隨著年齡的增長,我竟從中悟出一些道理來:生活中,有些事要抓緊辦,不能拖拖拉拉。這時(shí)你要像鴨子風(fēng)風(fēng)火火奔向稻田覓食一樣,抓住機(jī)遇不放。而有些事,欲速則不達(dá),不能操之過急。這時(shí)你要像大鵝一樣,自信又從容,耐心等待時(shí)機(jī)。
我以為,鵝是家禽里最懂得享受“慢生活”的。家鵝雖沒有天鵝的瀟灑與浪漫,但也不乏自己的優(yōu)雅與從容。我曾在詩作《立秋》中寫道:“雨,踱起了悠閑的鵝步/優(yōu)雅,從容”。可見,鵝對我的影響有多深。
牧鵝放鴨雖是童年往事,但那些動(dòng)感十足的畫面,卻時(shí)時(shí)浮現(xiàn)在眼前:一群“大腹便便”的肥鵝高昂著頭,踱著優(yōu)雅的小步緩緩前行;一群興奮無比的鴨子憋足了勁,撒開歡快的步伐向前急沖……牧鵝放鴨,綻放了童年的歡樂,蘊(yùn)含著人生的哲理,潛藏了溫馨的記憶。



















